晨曦中的招潮蟹:一种自然的召唤

四月春风吹来大海的气息,人在异乡,胃在故乡,但见成群结队的招潮蟹抬起大螯,一群又一群匍匐前行。

浩瀚大海中的小不点沙蟹,是地球数千种蟹类中的一小科,生存在热带和亚热带滩涂上、塘沽口、盐碱地和红树林,它们水陆两栖,行动疾速,营群集居。在我家乡玉环岛上,招潮蟹是沙蟹的主导品种,它们似乎效仿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作息,“潮退而出,潮涨而入”,极像有纪律的军团。它们的生命起源于白垩纪时期,躲过了大海中的帝鳄和其他凶猛的海生爬行动物,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
当四月的春阳给大海披上一层又一层金光时,滩涂一日日融暖起来,泥洞里的招潮蟹正上膏。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蟹螯痒了,当潮水退去时就钻出来,伸出大大小小的对螯,手舞足蹈,那副招摇的样子也许就是“招潮”之名的由来。它们或是在透口气,或是寻觅滩涂上的碎鱼、小虾、蚬肉……也有一出洞就以大螯叩响泥滩,发出求爱的信号,招引雌蟹的。站在海滩上可见百米外黑压压的蟹如排兵布阵般出来,蔚为壮观,看这架势,我乡人背起竹篓,带上网具赶潮去。
可招潮蟹耳聪目明,并非这么容易束手就擒,它有一对火柴棒头般凸出的眼睛,十分敏锐,听觉也是非凡地灵敏,能听到相隔十来米的脚步声,发现情况不妙就“哧溜”一下钻入洞穴,爬行速度惊人地快。当然,我乡人有很多诱捕的办法,他们用一种叫“大划”的捕捞工具,套着网兜的木质三角框上带着一把长柄,往滩涂螺旋状蟹洞眼插插划划;或是把系着诱物的绳子塞入洞内,把沙蟹牵引出来;也有的退潮前在浅滩上布下网具,退潮时把网收起,兜一网招潮蟹。最爽是在滩涂较干处眼疾手快冲过去徒手捕捉。总之一个潮汐捕一竹篓的招潮蟹很常见,但讨海人陷入泥滩的脚底也常被各种蛎壳割破,用黏性好的海泥敷上去止血,继续向海讨生活。
招潮蟹长方形青褐色的背甲隆起,极像迷你瓦片,味道不同于梭子蟹的甜糯丝滑,招潮蟹清口有奇鲜。到底有多鲜,鲜味作为蛋白质的信号和核苷酸的特质还没有量度,是一种感知。我小学班长阿平比我大四岁,他家就住在海边,他懂沙蟹的奇鲜。阿平常在春夏的周一上午从军绿色书包里掏出一个搪瓷罐,“铿锵”一声置于课桌上,早到的同学围过来,分享用火钳断了尾巴的乌螺(织纹螺),我一吮就连螺肉带鲜汁吸入嘴里,这吮乌螺比嗑瓜子更让牙根痒痒,每次都不过瘾,我实在忍不住就问阿平,为什么你能捡到这么多乌螺。阿平说我先从滩涂里抓几只沙蟹(口头语招潮蟹统称沙蟹),捣碎后在小水桶中稀释,赶海前到山边捆一束柳蒿,蘸上沙蟹水,放在泥滩上。乌螺闻到沙蟹的鲜气,就会奋不顾身爬过来,蒿草从滩涂上提起来,沉甸甸的,全是乌螺,如蚂蚁粘在糖果上。把乌螺撸入竹篓中。用柳蒿再蘸沙蟹水,转悠四五处,就满满一篓子乌螺了。招潮蟹的水汽就能让乌螺趋之若鹜,阿平用他的实战诠释了招潮蟹奇异的鲜。
少年时的美味记忆常常是最清晰的。我干妈有六个儿子,平常很少聚齐,说下海抓沙蟹,齐心协力,训练有素。根据潮汐或下滩涂或到塘沽口张网,每次都是满载而归。除咸腌外,他们也将蟹洗净做蟹胥,蟹胥即蟹酱,把蟹倒入石臼里,用木杵捣碎,加盐和蒜,再倒入黄酒搅拌,那种鲜香的气息飘在空中,左邻右舍端着一个小碟子拿着一个调羹笑盈盈地走过来,舀一调羮尝鲜。兄弟们把蟹酱装在玻璃瓶子里,少不了我的一份。这样的蟹酱吃起来香喷喷鲜嗒嗒,我想我刁钻的味蕾就是被这一瓶瓶蟹酱给娇惯出来的。
成年后在酒店里吃到油爆沙蟹,揭去肚脐边上的三角盖,整只带壳咀嚼,牙齿咬得咯嘣响,香香脆脆,好生鲜甜,原来熟吃也有另一番滋味。我曾买来做沙蟹咸粥,清甜鲜美。
江苏盐城有一道百岁菜,叫蟹豆腐,是用一种叫蟛蜞的小螃蟹捣泥细筛过滤除渣后,取汁液加蛋液等调料煮沸,再凝固成豆腐状。由此衍生出“豉油蟹豆腐”“宫保蟹豆腐”“海上生明月”等菜式,江南人在厨艺上总有别致的创意。仔细看来,蟛蜞形状极像家乡的招潮蟹,斗胆揣测它是海洋里沙蟹在陆地或淡水中的演变。广东潮汕人直称招潮蟹为蟛蜞,他们会做一道菜,让蟹浆分解,蟹浆凝固后下汤,有点像做鱼丸汤,汤面上漂浮着团扇形、云朵状或睡莲样的蟹浆片,我没有吃过,想想已是垂涎三尺。
现代人对食材和酱料是愈发讲究,把招潮蟹用清水浸洗,吐去泥沙杂质,用土烧白酒淋得它们从“招摇过市”到“醉生梦死”,这是一个消毒杀菌的环节,再用蒜蓉、生姜末、芫荽、紫苏等调香,加少许白糖,倒入黄酒、生抽、香醋,让蟹全部浸入汤汁,端起盆罐慢慢地撞晃,沙沙地震响,让汤料均匀地渗入每一只蟹,这样的招潮蟹,一口咬将下去,吮红膏嚼白籽,那真会把你的小舌头鲜得掉下去。
四月春风吹来大海的气息,人在异乡,胃在故乡,但见成群结队的招潮蟹抬起大螯,一群又一群匍匐前行,我的舌尖,亟待慰藉,我的故乡,美味道不尽。(叶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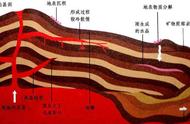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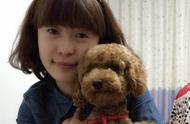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