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一生追求美的勇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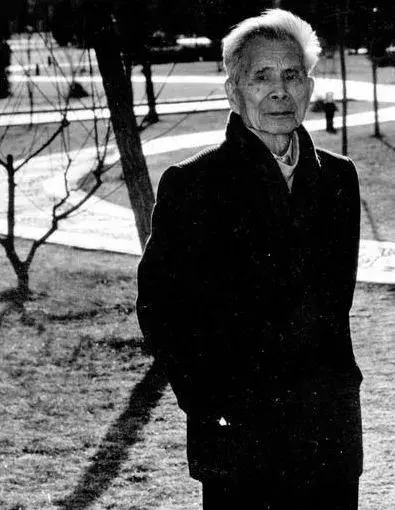
吴冠中,第一位获授“法国文艺最高勋位”的中国籍画家,中国画坛“最后一位大师”。

吴冠中童年
1
吴冠中小时候,
家到学堂的路上有一座石桥,
“桥下,是拥挤的船帆。
船帆近大远小,最远处,
便成了一个小点,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
这是吴冠中的第一堂美术课,
“它就像鲁迅笔下的乌篷船,
亲切而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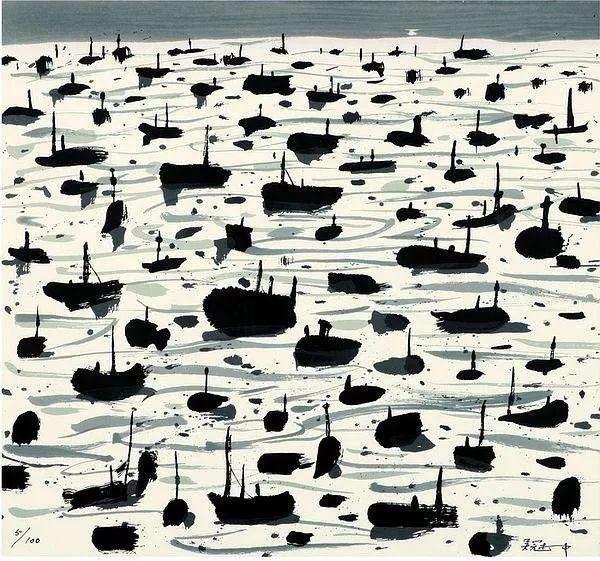
《渔港》
每逢过年,一个叫缪祖尧的老画家,
总会来吴冠中家作客,
“我经常去缪老师家看他画画,
他的画室窗口掩映着绿油油的芭蕉……”
这是吴冠中的第二堂美术课,
“我接触到了绘画之美。”
吴冠中的母亲是个文盲,
但她极具审美天赋,
“她给我织过一件毛衣,
她织了拆,拆了织,费尽心思,
那件毛衣如同艺术品一般别致。”
这是吴冠中的第三堂美术课,
“哪怕是一个文盲,她也不一定是美盲,所有人都爱美。”

留法三剑客(从左至右):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
17岁,吴冠中认识了朱德群,
后者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
一天下午,他带吴冠中去参观艺专,
艺专里,到处都是图画和雕塑,
“我感觉受到异样世界的冲击,
就像婴儿睁开眼初见的光景。”
这是吴冠中的第四堂美术课,
“美如此有魅力,十七岁的我轻易拜倒在她的脚下!”
父亲坚持让他读工业,
而他不得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
然而悲伤也挽救不了我这个受诱惑的浪子。”
他满怀苦涩违背父命,
考上艺专,走上人生“歧途”。

《夜宴越千年》
2
一开始,吴冠中的写生课从国画入手:
苏堤垂柳、断桥残雪、平湖秋月。
当时的校领导,
几乎清一色都留法回来的,
因此校图书馆里的画册和期刊主打法国。
一个异样的世界深深吸引了吴冠中,
“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在17岁的年纪,
我就爱上了那些不为国人熟知的大师。”
学校同时开设了法文课,
黄纪兴担任法文老师,
“很多学生连中文都困难,
见了黄老师都躲着走。”
吴冠中却无比珍惜这门课,
“学了法文,就有机会去看看梵·高。”

吴冠中与朱碧琴
毕业后,吴冠中在重庆大学任教,
期间,他邂逅了来自湖南的朱碧琴,
两人相知、相恋,步入婚姻殿堂。
就在这时,教育部准备组建战后第一批留学生,
当中有一个留法绘画的名额。
重大校长张洪沅找到吴冠中:
“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的中转站,如不前进,便将淘汰。”
这番话,坚定了吴冠中留学的决心。
最终,吴冠中争取到了唯一的名额;
与此同时,朱碧琴也分娩在即。
一边是大肚子的爱人,
一边是法国梦的召唤,
吴冠中再一次深陷抉择的痛苦。
朱碧琴把祖传的金镯子卖了,
给吴冠中买了块表:
“去吧,远渡重洋,有个手表方便。”
她又把一件赶织的毛衣递给吴冠中,
黯然转过头:“除了我,再不会有人愿意嫁给你。”

1947年赴欧洲留学生
3
1947年夏,吴冠中一到巴黎,
就如饥似渴冲进了卢浮宫。
他一人在断臂维纳斯面前看得入神了,
管理员突然走过来问他:
“在你们国家,没有这种珍宝吧?”
面对管理员的高傲神情,
吴冠中急了:“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来的!
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
就藏在吉美博物馆!”
向往法国,法国却中伤了他,
这让吴冠中有些受不了,
“我感受到不得不用法语跟对方吵的羞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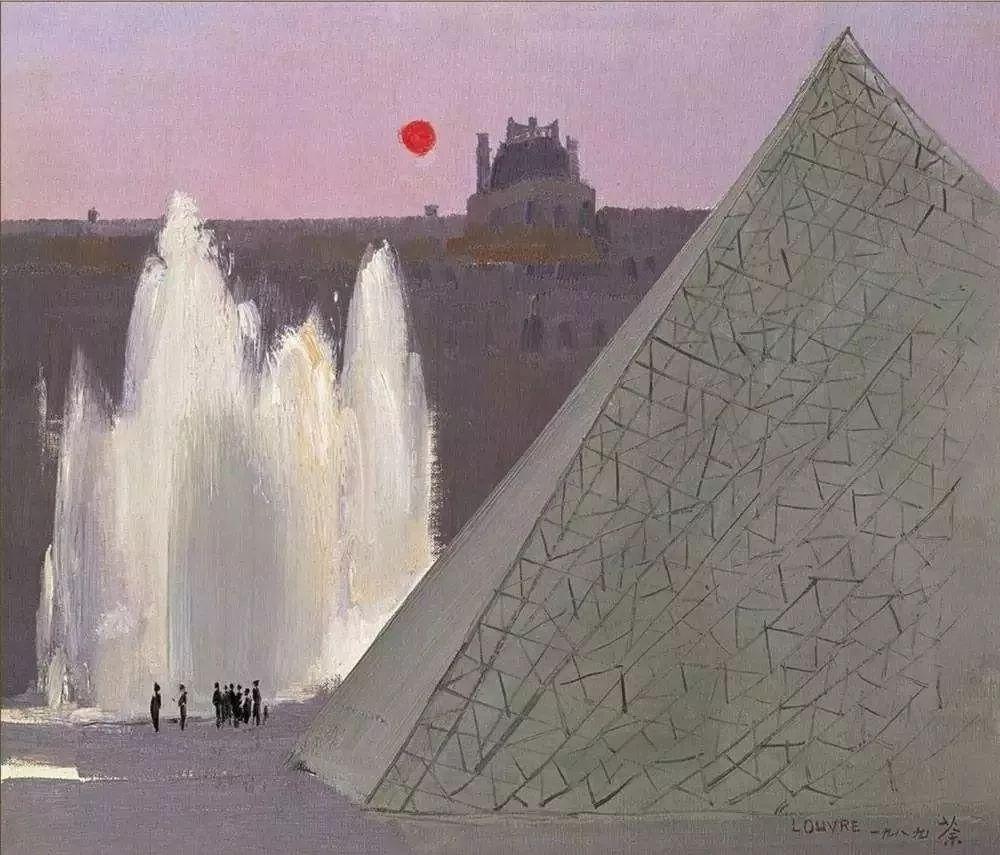
《卢浮宫》
跟国内画国画不同,
在巴黎,主要画油画,
绘画的对象主要是裸模。
“有次来了个青年女模特,
大家称赞她形体很美,
但只来了三天,她就不来了,
她投塞纳河自杀了。”
吴冠中第二次意识到,
法国并非看起来那么美好,
“她那么美,美却害了她。”
有次旅行坐公交,
他用硬币买了票。
“售票员把硬币捏在手里,
转头向我邻座的外国人售票。
他给的纸币,需要找零,
售票员顺手将硬币找给他,
他却生气地不接受,
他无法接受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的钱。”
第三次的恶意,让吴冠中的乌托邦崩塌了,
“它像一把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
我曾千万次对法国怀抱憧憬,
而今付出的是羞耻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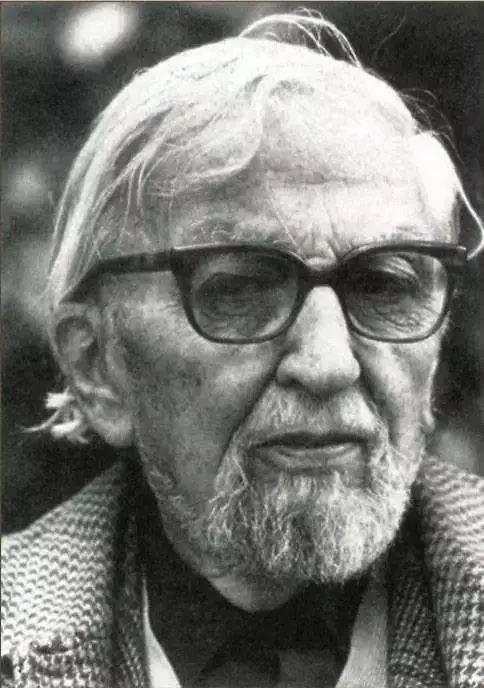
苏弗尔皮
当然,他在国外也遇到过美好的一面,
吴冠中的老师叫苏弗尔皮,
“他的作品从‘形式’入手,磅礴而沉重,
主题都是对人性的颂扬。
是他开启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力度的认知。”
苏弗尔皮将“形式主义”倾囊相授,
但老师的挽留也救不了“浪子”的归国之心:
“我吃了三年西方的奶,
但却挤不出奶。
我必须回自己的山里去吃草,才能有奶。
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画室,
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
在自己的心底。”
苏弗尔皮只得放手:
“回去吧,像梵·高说的,
做一粒麦子,
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

50年代的吴冠中和三个儿子
4
1950年,吴冠中回国,
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他把自己的绘画对象定义为“人”,
他先画了一个农民给大家看,
“我在画中的农民胸前画上一朵大红花,
但后来反映很不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
面对大家的批评,
吴冠中却坚信“形式大于内容”:
“作品只是内容的本身,
它毫无灵气。
而恰当的形式运用,
就能赋予内容的灵魂。
内容是小路艺术,它只能娱人;
形式则是大路艺术,它可以撼人。”
一次批评,吴冠中毫不在意,
他又以“形式主义”画了工农兵,
被大众批判为“丑化工农兵”,
“我与群众和领导隔着河,却找不到桥。”
再次被批评后,
吴冠中坚持以“形式主义”授课,
没多久,有学生状告吴冠中,
说他是资产阶级文艺观。
一次全院师生大会上,
前辈徐悲鸿直接发话:
“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
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
这次批评后,美院再也容不下吴冠中,
将他调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因为建筑不是人,不怕形式主义。”
在清华,吴冠中教素描和水彩,
“我以往只注重油画,瞧不起水彩,
为了教好课,我不得不在水彩上下功夫。
我将水彩和中国水墨相结合,
然后画了一棵树,
发现那棵树居然有了人的喜怒哀乐。”
吴冠中找到了连接中西方的桥:
用水彩、水墨和油彩,画风景,
如同建筑,风景也不在乎“形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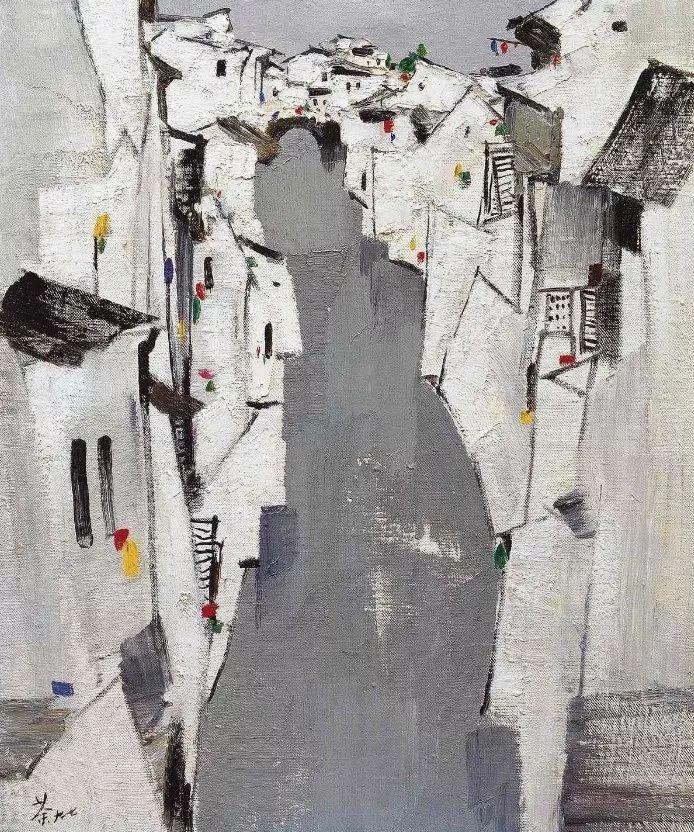
《水巷》
5
爱上风景画后,
吴冠中最期盼的就是寒暑假。
届时,他背着油画布、三合板,
独自深入大山深处,
去探索更多的形式美,
其间,他吃尽苦头。
“山里风雨难料,阵雨来了,我就撑开身体遮挡油布。”
有次从海南岛椰子林作画回来,
发现写生架丢失了一个铜钩,
“写生架有两个铜钩,缺一不可,
这简直五雷轰顶。
第二天,我沿着昨天作画的路线找回去,
居然让我找到了。
我捧起染着颜料和朝露的铜钩吻了又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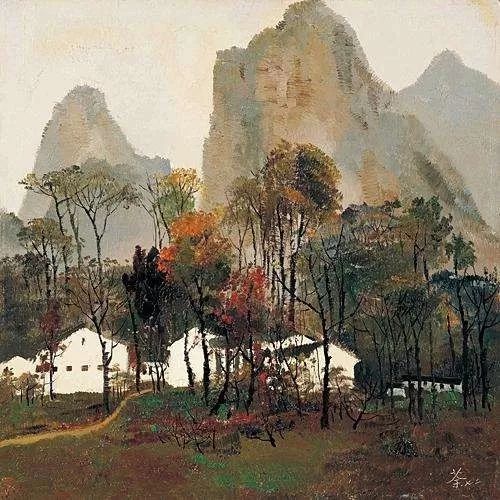
《桂林山村》,“移花接木”的形式民族画
在西藏,他找到了答案。
有个青年战士接他去唐古拉山,
“一路上,雪山、飞瀑、高树、野花穿插其中,
构成新颖奇特的画境。”
第二天,战士和吴冠中又去了,
但这次是坐车,
“4个小时的路程,缩短为20分钟,
路上好多景色都不见了。
我恍然大悟:速度改变了空间,
不同位置的山、村和林被速度综合起来,
组成了引人入胜的画境。”
“移花接木”,成为吴冠中作画的第二个灵感,它让绘画有了律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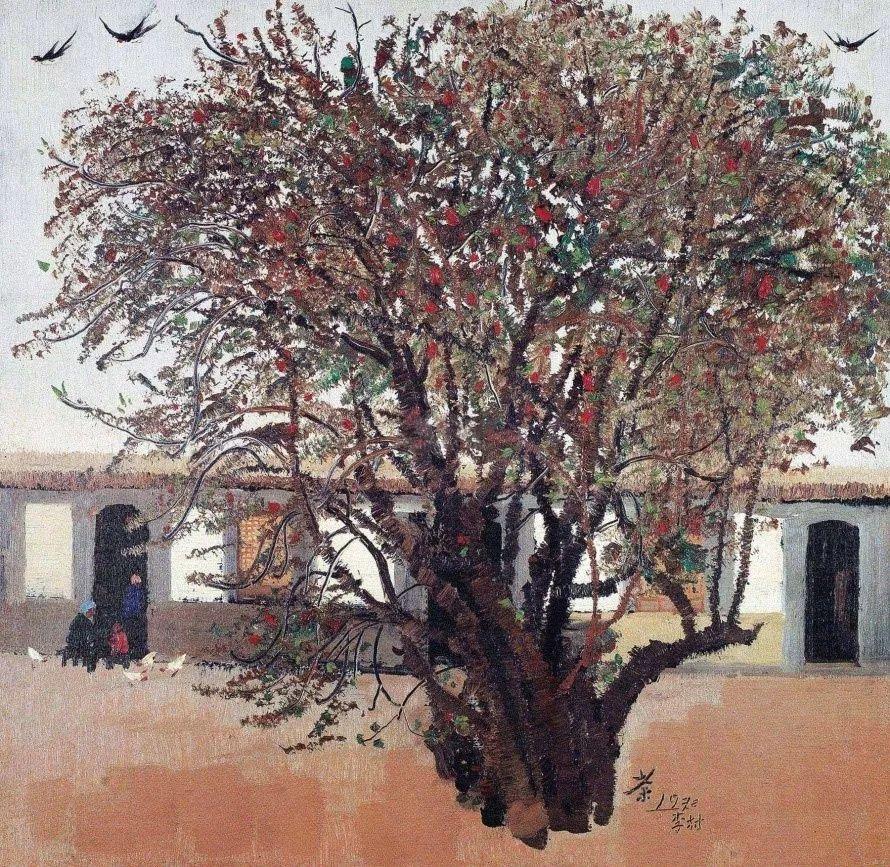
《房东家》
6
因为常年待在深山老林,
吴冠中被查出肝炎和脱肛,
每晚痛得睡不着觉。
朱碧琴见他这么痛苦,
临睡前就摸他的头,
“她说,这一摸,你就睡着了。
她从来不撒谎,竟也撒起这样可笑的谎来,
而我竟也不觉得幼稚。”
没多久,“文革”爆发了。
因为“形式主义”,
吴冠中被下放劳动改造,
他和爱人、三个儿子被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
改造过程中,脱肛尤为厉害,
“痛得不能走路,
我用布和棉花做了一条如同月经带的带子,
缠在肩上,绕过胯下。”
就这样,吴冠中坚持了两年。
两年后,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
但病情仍没好转。
吴冠中觉得人生完了,
他决定以全身心作画的方式自杀。
“我用老乡的粪筐做画架,
日以继夜地画玉米、高梁、棉花……”
他被老乡们戏称为“粪筐画家”,
他的“粪筐”作品后来大多流落到海外,
成为收藏家们的心头爱。
做“粪筐”画期间,
房东、大伯大娘、小孩成了他的作品鉴赏者。
“他们很善良,
当我画糟了,
他们会说画得很好、很漂亮;
画成功了,
他们则会开心叫起来:真美呵!
他们很多跟我母亲一样,
都是文盲,都不是美盲。”
就是这群“文盲”,
让吴冠中相信老师苏弗尔皮的论述——
“漂亮”和“美”是不一样的,
“漂亮是肤浅、是警惕,
而美,是赏心悦目。”
这群文盲,让吴冠中获得第三个作画灵感:
作品一定是有母体的,
这个母体,就是符合人民大众的“美”。

《苏州狮子林》
7
60年代初,吴冠中最爱去的地方,
是江南的村落,
“中学时代,我最崇拜鲁迅。
虽然我不能写出《故乡》,
但我可以画下江南。”
他在江南画了不少山水,
但始终不太满意,
因为江南风光不适合用油墨,
而只有水墨,又缺乏新意。
“文革”一结束,他的病情好转,
就带着学生钟蜀珩一起到江苏、下江南。
有一次在苏州园林,
吴冠中整个下午都不见钟蜀珩,
直到听到她的叫喊,才在一个假山的高处看见她。
原来,她被锁在了园中。
她说:“当我急着在园里瞎转时,
我才发现园林这么美。”

《双燕》
这段话,给了吴冠中意外的启发:
“我们作画都太注重手了,而忽略了‘眼’是‘手’的老师。”
他得到了民族画创新的第四个灵感:眼高手低,
手技随眼力高低而千变万化,
思想则通过眼睛,驾驭手里的工具。
他再度来到江南,
跟其他画家一样,用水墨作画;
但同时,他运用了西方的简约几何作分割,
让作品只有黑白的虚实冲击,
线条纵横的交错对比,
外加一双沧海蜉蝣般的小燕子。
这幅画,就是吴冠中的巅峰作之一:《双燕》。

《武夷山村》
8
作《双燕》的同时,
吴冠中又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武夷山村》《苏州狮子林》《春如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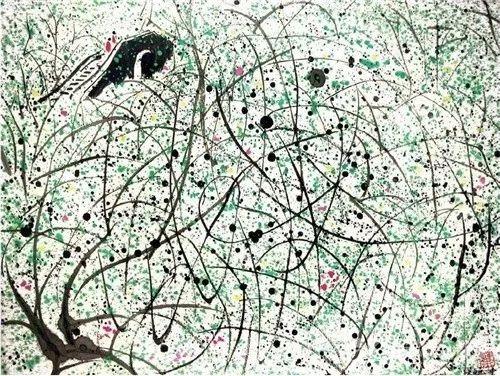
《春如线》
乍一看,这些画风马牛不相及,
但仔细看,它们其实是同类:
它们将画面抽象,
而主题就藏在抽象里面。
这是吴冠中作画的第五个灵感,
他将其归纳为“风筝不断线”。
“风筝放得越高越有意思,
但不能断线,这线,
一头牵的是抽象技巧、笔墨,
另一头牵的则是人民的真实情意,和画的主题。”
《双燕》《春如线》这类画,
无不是在几乎被忽略的地方点题。
或许有人觉得中国不需要抽象画,
但吴冠中更希望推翻成见:
“我追求全世界的共鸣,
更重视十几亿中国儿女的共鸣。
艺术的审美不该是单调的,
高峰的艺术是相通的,不分东西方,
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的风光不同,
但终会在山顶相遇。
白居易是通俗的,接收者众,
李商隐的艺术境界更迷人,但曲高和寡,
而我,两者都要。”

9
80年代开始,
吴冠中开始不断地毁掉他的部分作品,
“我的很多残次品流入了市场,
被人重金拍卖,成了商品。
艺术品最终成为商品,这是客观规律,
但在一时盛名之下,
往往不够艺术价值的劣画也都招摇过市,
欺蒙收藏者。
毁画就像屠杀自己的孩子,
但与其让它们成为捞金的工具,
不如我亲手毁了它们。”
最出名的,就是1991年,
吴冠中一口气毁了几百幅“次品”,
被外国人称为“烧豪华房子举动”。
那段时间,他感觉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欲望,
无处打发空虚,
就钻研画家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
十几岁开始,他就崇拜石涛,
但当时他学问有限,看石涛如读天书。
现在,他读懂了石涛的“一画之法”:
“一画之法有三个核心,
一是尊重自己的感受,
二是技随人生,人灭技灭,
三是一法贯众法。
总结起来就是,
在千变万化的感受中,表达自己当下的画法。”
这成为吴冠中最终极也最重要的作画灵感:
无法之法,乃为至法。

《周庄》
1997年,吴冠中画出了《周庄》,
它是《双燕》的江南姊妹篇,
也是吴冠中的压轴之作。
这幅画里,看不到任何具体的形式和画法,
却又充满各种形式和画法:
里面有江南的写实内容,又有点线面的抽象形式,
有东方的水墨洇染,又有西方的油画写意,
有宏观的高墙黑瓦,又有微观的惬意生活,
有沉静隽永的静物,也有水流环绕的动景……
它是“不断线的风筝”,
它将静景与涌动的人和白云“移”在了一起,
它将“形式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它同时拥有了白居易和李商隐,
它把东西方的壁垒敲碎,
它以无法,胜却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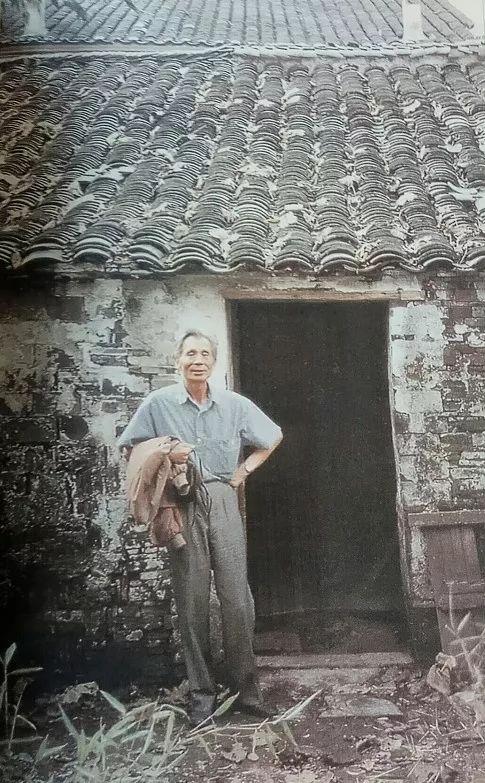
吴冠中故居
10
1981年,吴冠中赴邀去巴黎,
见到了朱德群,
两人少年相识,再见却已两鬓斑白。
当时,朱德群已是法国国籍,
在当地已经功成名就,
“留法三剑客”的赵无极亦是如此。
而吴冠中呢?选择回国后,
一生坎坷,被举报、被批斗、被改造,
三十多年里,“如猎人生涯,深山追虎豹,弯弓射大雕”,
到老了还被商业社会利用。
有一个朋友问他:“如果你当年不回去,
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吗?”
吴冠中摇摇头,没说话,
但这番没说出来的话,
他早和爱人说了无数次:
“留在巴黎的同学借法国的土壤开花,
我不信种在自己土地里的种子长不成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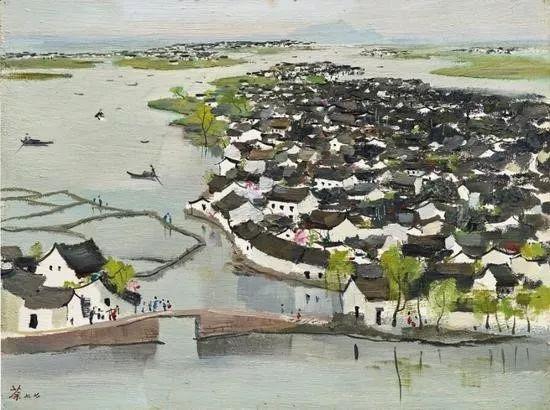
《鲁迅故乡》
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
首次为一位华人画家举办了绘画展,
这个华人,就是吴冠中。
对于此次展览,英国媒体报道:
“凝视着吴冠中的一幅幅画作,
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
是近数十年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发现。”
吴冠中的种子,终于长成了树,
他为国家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艺术价值,
而这些价值反馈给了他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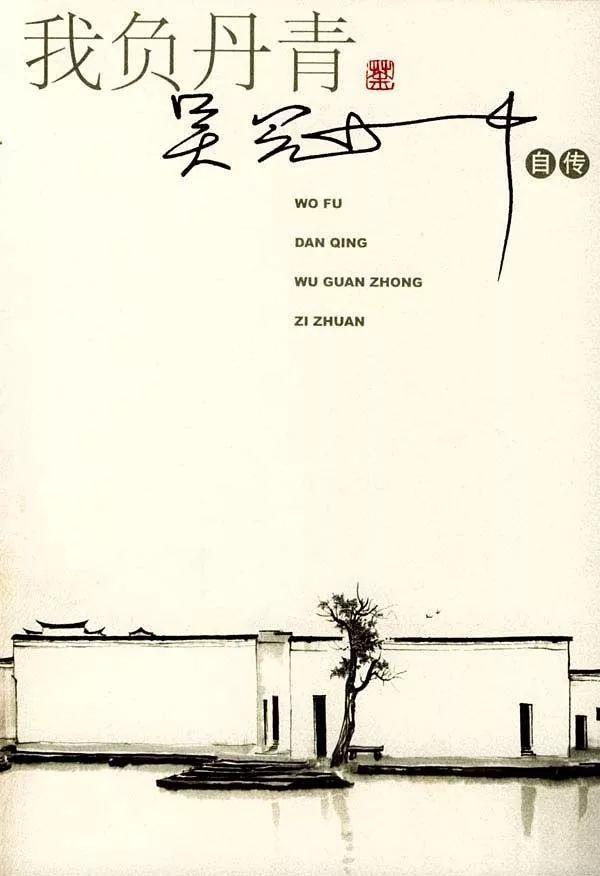
人生最后几年,
他把所有作品都无偿捐给了国家,
自己则在病隙中拼命写个人传记《我负丹青》,
“我写下这份真实的资料,
以备身后人知晓一个真正的吴冠中。”
2010年,吴冠中去世,享年91岁。
儿子吴乙丁回忆:
“遵照父亲的遗愿,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
父亲走时,
穿着他平时喜爱的朴素衣物,
唯一的陪葬品,就是《我负丹青》。”
“我负丹青”,是他辜负丹青了吗?
不是的。
“我负丹青”,
是他背负了中国丹青的使命,
是他要把油画努力实现民族化的夙愿,
是他希望能够推翻各国对于美的成见,
是他感知时日无多而画无止境的喟叹。
“在我躯体走向衰颓时,
情感却并不日益麻木,
甚至翻腾着波涛。
这些波涛本是创作的动力,
但它们冲不动渐趋衰颓的身躯,
这是莫大的悲哀。”

20岁时,他身躯正盛,
拥有使不完的力气。
那时候,他还在杭州艺专,
无限崇拜梵·高、高更,
崇拜他们的作品,
也崇拜他们那颗并未被苦难所击倒的热爱之心。
他遂取笔名为“荼”。
荼者,尝尽世间之苦也,
而后的生活,也如这个字一般,
苦苦缠了他大半辈子。
他呢?他只提了四个字:
嚼透黄连。
这世上就有这么一种人,
只要没有被击倒,他就能继续地笑,
继续地燃烧,继续地翻搅浪潮。
名利啊,富贵啊,
重要吗?
重要,但对他们而言,
更重要的是,
既然心火已点燃,
就别让它熄灭;
或许情不知所起,
但请一往而深。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