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明揭秘:高庙文化陶器图像揭示的宇宙观溯源

【考古中国】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楚辞·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记载了先秦时的宇宙观,说的是天为圆形,有九层;天上有网络,以天极为中心枢纽;天体围绕天极旋转。这种强调天极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的宇宙观,可以称作“天极宇宙观”。
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装饰有内涵丰富的戳印图像,表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天极宇宙观”已经初步形成。
八千年前的“天极宇宙观”
高庙遗址出土的一件白簋的器身上,有复杂的戳印图像:中心为简化的兽面,突出表现一张大嘴和四颗獠牙,内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嘴上方有两只小眼睛,下垂部分为舌头。兽面外有圆圈,圈外以不同图形分出八方。左右方向为简化的圆形鸟头,以短横线表现鸟喙,以小圆点表现鸟眼。鸟头上凸出的部分,可能表现的是羽毛。上下方向为尖顶屋宇形。四角方向均为长方形框内加尖顶形状。

高庙遗址陶器上彩绘的吐舌獠牙图案 选自《洪江高庙》
对于这样中央有特殊图案、圆形环绕中央、圆形外分出八方的构图,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宇宙观的图像化表达。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相关神话中,鸟一直是重要的动物。器身两侧的鸟纹,更加强了这类图像与宇宙观相关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个神奇的图案中,位居中心的阔口獠牙,占据的明显是天极之位,应该是控制天极的神灵的动物形象。考虑到对四颗獠牙的夸张表现,兼之此后与天极宇宙观相关的玉器中常见虎的形象,此动物为虎的可能性很大。
高庙文化陶器戳印图像最重要的主题,是胸口和翅膀上有獠牙大嘴和其他图案的神鸟。这些神鸟都有巨大的钩喙,双翅或向上扬起,或向两侧展开。最神奇的是,鸟翅膀及有些鸟的胸口上有完整或一半的獠牙大嘴图案。鸟翅膀上,还常见中心有圆点或者十字、外面有圆圈和表现四面八方的符号,都是代表位居天体中心、为各方向起点的天极。一些器物的底部,还刻画着八角星纹和十字纹等,也都代表着天极。

红山文化的玉勾云形器 李韵摄/光明图片
我们推测,高庙文化时期(距今7800—6600年)天极宇宙观包括以下核心内容:一是天极为天体运行的枢纽所在,以圆形中心的八角星纹、纽结形纹等形式表现;二是天极之神控制着天极,维护着宇宙秩序,其动物形象为虎,典型表现方式为獠牙兽面;三是天极之稳定需神鸟维护,表现为神鸟驮负或环护天极。
值得关注的是,高庙文化的这些特殊图像流传很广。江苏淮安的黄港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高庙文化风格红胎白衣陶器,上面戳印着同样的神鸟图像。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也发现了獠牙兽面的形象。可见,高庙文化在“天极宇宙观”的起源和流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极宇宙观”成为宗教信仰的核心
“天极宇宙观”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史前时代进入转折期,各地区社会跨越式发展,形成“古国”。长江流域的凌家滩社会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选择“宗教取向”的发展道路,“天极宇宙观”成为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社会的领导者宣称自己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可以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的通灵状态下,实现与神鸟的沟通转化,维护天极的稳定和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自然可以聚集社会资源和财富,建立被称作“古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大规模人群。

良渚遗址出土玉牌饰上的神徽 李韵摄/光明图片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为红山文化的仪式中心。在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未见大型居址,散布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等仪式性建筑。积石冢中随葬刻画神鸟驮负獠牙兽面的玉“勾云形器”,表现的正是神鸟对天极的维护。以玉制作的蝈蝈、蚕蛹和蝉等昆虫,以及屈腿收臂、处于蜕变状态的玉人,均展现了佩戴者蜕变通天的宗教能力。
凌家滩遗址玉版上的刻画图像,如同“天极宇宙观”的图解:两重圆圈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大地,中心圆圈和外层圆圈间的八条“圭形纹饰”为连接两重天的绳索,同时表现八方。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圭形纹饰”如同维系天地的四维。中心的八角星纹,正是天极的标志。凌家滩玉鹰,双翼为代表北斗星的猪头,胸部刻画八角星纹,表现的是神鸟维护天极、北斗绕天极运转的主题。
距今约5300年兴起的良渚文化,将以“天极宇宙观”为核心的宗教系统规范化,完成了早期国家构建,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重要实证。良渚文化玉琮是为了表达“天极宇宙观”特意设计的特殊玉器。精雕细刻的神人兽面像,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神徽”,表现的是良渚社会领导者正在转化为神鸟,将天极神兽驮在胸口的神圣场景。完整的“神徽”只出现在最高等级的“王墓”中,表明良渚王者对沟通天极之神的最高神权的垄断。

陶寺遗址观象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距今约4300年,良渚文化衰落,但其系统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中,均流行獠牙人面图像,应是人格化的天极之神形象。肖家屋脊文化的写实虎头图像、虎头镂空牌饰和虎侧身像等,是对天极之神动物形象的写实表现。
坐落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则提供了以“天极宇宙观”宗教构建早期国家的明确证据。位居遗址核心位置的皇城台地点,顶部为大型石砌祭坛,是刻意打造的与天极之神沟通的神圣地点。石雕主题中,也发现了处于向神鸟转化状态的神巫与猛虎形象的天极之神沟通等场面。
“天极宇宙观”与“天下政治观”
与古史记载中尧的活动中心相符的陶寺文化,似未选择宗教取向浓厚的社会发展策略。但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玉琮、玉璧及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镂空神像和蝉。陶寺高等级墓出土的陶器上,盛行以鸟为主题的彩绘,遗址南部还发现了天文观测设施。《尚书·尧典》记载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陶寺领导者由“天极宇宙观”发展出“天下政治观”、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政治实践留下的历史记忆。
商代甲骨文中的“帝”字,被解释为天极周围的星象或花蒂的象形。可见,商人信仰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帝”,正是由天极之神演变而来。商人称其都邑为“中商”,《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以天极比喻都邑在天下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周边地区则被称作东、西、南、北“四土”。正如天上有靠近天顶的拱极诸星和外围星宿一样,商将自己掌控的“天下”分为“内服”和“外服”,“天下政治观”开始被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宏大政治理想的形成和落实,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特质,是历史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源头。如此宏大的政治理想的形成,得益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空间辽阔而多元,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也得益于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有自身的“裂变”,也有相互的“撞击”和“熔合”。但不容忽视的是,高庙文化孕育的“天极宇宙观”及其向天下政治观的演变,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0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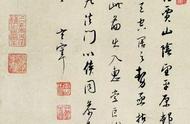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1号